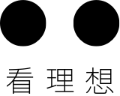你好,童年
正文
03. 印度:在混乱中抓取秩序,在大环境中各自努力(上)

30:23

82
收听提示
1.周轶君在印度遭遇了什么,让她又“崩溃”又“傻掉”?
2.美国的“影子校长”是什么?
3.“留守儿童”到了寄宿学校,会发生什么?
本期嘉宾
梁文道
“看理想”策划人,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主讲人。
王世民
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新镇小学校长。他筹措资金办起陕西省第一所公办寄宿制小学,关注国外教育,曾在美国农村当“影子校长”。
正文
周轶君: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童年》,我是周轶君,今天我们两位嘉宾都非常的有意思,在我的左边是王世民校长,他来自于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辛镇小学,他是筹措资金办起了陕西省第一所公办的寄宿制小学,不但如此他还特别有意思,他曾经在美国的农村当过“影子校长”。
在我的右边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其实是我这个所在地的地主, 看理想的策划人,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的主讲人梁文道。
梁文道:对,我是打酱油的,其实是,路过。
周轶君:为什么请梁文道呢?也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谈一谈印度的教育和由此生发出去的很多很多的话题,那么我知道文道一直是非常关心印度。
梁文道:我是印度迷。
周轶君:曾经发愿要赤脚要走印度。
梁文道:没错,一直没走成。
周轶君:刚才我本来是想从王校长这边先开始,但是刚才听到了文道说看完了印度一集,对我有很多的批评,好,我要先接受批评!
梁文道:没有,主要是这个你的声音咳得太厉害了。有时候这个声音收得不太好,我觉得收音,然后调音没调,这后期问题不关你的事,都是其他人的问题,怎么会是你的问题。
周轶君:不是,你这个说得非常专业,因为这个就涉及到我会要解释一下我们在印度的工作情况,你看得太专业了。
梁文道:我都是看这些,内容,那没话讲,那简直太厉害了是不是?
周轶君:我先跟你讲讲说收音这个事情特别有意思,我们在印度,因为我去每一个地方都用的是当地的摄影师,原先不是这样计划的,但后来赶巧就变成这个样子,尤其去印度之前刚好是印度跟巴基斯坦在发生冲突的时候。
梁文道:我记得那阵子。
周轶君:对,我们片子里其实有提到,然后我本来请的摄影师他们就很麻烦,因为很多机场关了签证也很难拿。那这时候我就说那就请当地的这个摄制组,我还想说印度应该没有问题,都拍宝莱坞那么多电影对不对?
我想拍摄应该没有问题,从器材到人都应该很好找,结果就发现了其实他们对于纪录片的形式是完全没有概念,他一听说要拍片就是宝莱坞大制作,一开始所有的制作公司给我开出来20个人的单子,说要一个20的团当中还要我去买帐篷,买塑料椅子,我说这是干什么?
而且是每天要准备20个人的餐食和茶点,下午一定要喝茶。我说这是干什么?他们说塑料椅子和帐篷是你到一个地方,你导演得坐在那里,很多人要围观你得坐。
当中还包括说,除了这20个人以外,到每一个地方有那个spot boy就是当场的男孩什么的,就你随便可以抓三个小孩帮你看东西,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到哪都能找到三个小孩,他说一定有就是游手好闲的,这些小孩一定有,他不上学或者干嘛。
而且印度他们的保险制度很差,你租器材的时候,比如说我说我付一定的保证金,对吧?我就可以把它带走,因为我要飞很多地方,那不行,所以一定要一套器材两个人跟着你,因为他两个人相当于他的保险金。
我说可是两个人跟着我,我还要飞啊什么,他说那不管,一定要有人跟,到最后的最后我们就是减少到我那个组是七个人,七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跟着我们一起飞,他的所有的工作只是看着那一堆相机,如果出事就是他的问题。
梁文道:这个就是他的保险费。
周轶君:对的,那么这个七个人的摄制组是在我所有不同国家拍摄当中最多的一次,那么我在这个加尔各答的时候就是头几天拍摄真是领教了他们的工作方式,你说到这个收音的问题,我们在加尔各答请的第一个收音师在拍的时候,每次都在跟我抱怨说他需要助理,说人手不够,而且每次开拍了人找不到。
好了,这些都过去了,到最后我们在头两天拍完要离开那座城市的时候,我还在犹豫我要不要带他飞的时候,当时已经跟他结账什么都弄好,感谢他,他最后告诉我说,顺便告诉你一句,我所有的收音都没有同步,就是跟你的画面都没有同步,他当时没有做拍手,也没有做就是同步的那个音轨那些。
我说为什么你现在才告诉我?他说我之前不好意思告诉你,我说那你这个回去我会被后期的剪辑师要骂死的,因为他要一个一个对啊,后来我知道印度人是这样,他们其实有一点点跟中国人像的地方,就出了问题,他不太敢说。
梁文道:没错。他们比我们厉害。
周轶君:怎么厉害?
梁文道:就更严重,他不说。
周轶君:他不说,那到后来我又请了一个比较好的收音师,据说是整个印度最好的收音师,第一天第一场拍的时候正在访问,有一个人的手机响,我们发现就是他,我说你收音师最不应该手机响的。
然后我们整个七个人团队他们是来自于不同的种姓,每个人都在背后会讲另外一个种姓的故事等等。我也是这一场印度之旅对这个国家的这种多样性的文化有了很多的理解,但他们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一开始的时候主摄影,他在拍摄当中忽然发现拍着拍着没有电了,那一般摄影师身上会揣两块电池,换掉就可以了,他要回头叫助理A:“电池”,助理A进来看一看叫助理B:“电池”,换一个电池要三个人。
我们就傻掉了,访问要停在那里等他换电池,我说你身上不可以带电池吗?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个含义是什么?他们有一个等级制度。
梁文道:是的。
周轶君:这个等级制度贯穿在这么小的事情里面,就是他自己作为我是主摄影,我是艺术家,我不可以换电池,他拍完的时候他的手里面是不可以拎着这个摄像机,他一定要有人帮他拿,所以导致我们拍的时候,比如突然看到一个什么场景想拍,他是要找,“我的机器呢?”
所以在印度一开始那头大概十天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崩溃的,就觉得效率太慢了。但是到最后慢慢相处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之前看那本书讲印度的叫《不顾诸神》那本书,它里面有个总结,说印度人是这样的,当你身在其中的时候,你觉得是一团蜜蜂在乱飞,不同的方向,你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茫无头绪。
但是当你后退一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虽然很慢,但所有的蜜蜂在飞往一个方向,我们在那里虽然中间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在印度所有的拍摄计划居然到最后也是全部完成的,我也非常惊讶,非常惊讶。
梁文道:Everything will be fine,这个是印度的信条。
周轶君:不要着急不要生气,最后都可以做出来。
梁文道:虽然你看起来他们很乱,好像很没有制度或者很多等级很无谓的东西。但是当到了有必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很变通地弄出很多东西来,把事情还是完成。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就跟印度你这期节目里面讲到他的教育,我觉得可能有关系的,是因为他们的整个教育里面贯穿了一种非常灵活的。
周轶君:他们叫jugaad,随机应变解决问题,那王校长,您看的时候你好像对有觉得印度的那种情景,虽然您没有去过,对您自己的教学在中国乡村啊等等有呼应吗?您觉得?
王世民:其实我去年,2018年去夏威夷的时候,其实现场听了那个苏卡塔教授的讲座。
周轶君:这么巧,就是我节目里拍到的那一位教授,他做互联网教育。
王世民:其实他这个墙上洞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小孩是可以自己学习的,就是自主学习,在我们学校,有时候给我们就是年级里边比较很厉害,那些孩子讲,我说你要将来要当博士的话,你就必须自己去学,因为我们是教不了你去成为博士的,因为我们是本科生。其实苏卡塔教授这个理论,就是孩子们天天生自主学习这个能力。
周轶君:您刚刚说的这个“墙上的洞”,我来解释一下,这个计划是在九零年代,就是苏卡塔博士先是在印度的,是在新德里还是孟买的贫民窟里面,他给孩子装平板电脑,在墙上装电脑嘛,就让他们自己去上网去找答案。那么那些孩子其实根本没有机会去上学的,但是他直接接触了互联网,那么这些孩子这个故事后来是直接启发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个电影的作者。
梁文道:原作者。
周轶君:对,他当时是一个这个外交官,他看到这个故事以后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他创作那个电影里面的人物也是一个身处贫民窟,但知道很多乱七八糟的知识的自学而来的这么一个孩子。
王世民: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片子里边就是思辨,就遇到问题,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想起我们学校就是孩子比较多,有40多个班,吃饭前有一个是要做的,必须要去洗手。就是在以前就是老出现这个水龙头的问题,一个学期坏好多水龙头,因为一个孩子要去把那龙头水要开开。
结果我们最后也就想就是在一个铁管子上面锥上孔,一排四十几个孔,只有一个开关,然后一个班40多个孩子过来以后,全部就可以节约时间,还节约资金,我觉得这个Jugaad跟我们还是有相像的。
周轶君:就是他们说的,没有莲蓬头,自己拿一个铁皮桶捅几个窟窿,你们也是在水管上捅几个窟窿。
王世民:这个就是思辨,我觉得对我们启发还是比较大的。
周轶君:那您觉得就是让孩子就相信他们自己去学习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一些具体的做法?我看到很多家长,比如说他们其实把孩子所有的时间都占满了,他们不停的去学习,但其实我觉得他们很满。当他很满的时候,可能不太想去学,有的时候。
王世民:我一直给家长在进行家庭教育的时候,我一直跟他们讲,我就说我1小时的课不如让他们自己去读30分钟的书,我一直强调这个观点,但是从学校这个层面上去讲的话,就是让孩子能够轻松。
小学生们玩是他们天性,要保证他们有时间去玩,当然还要让他们要学得好一点。其实我想就是我们这几年做的自主学习这一块,我觉得我们还是五六年的时间还是有好的效果,有些课,就是小老师讲课,这节课就是由他们前期去准备,老师把一些问题设计里面,让他们在上面去讲,这是一个。
梁文道:同学们自己当小老师。
王世民:自己当老师去讲,他要去当老师,他还在课堂上去讲,他准备的那种认真的态度,精心的程度,可能我们有的老师有时候就觉得可能还是做不到的。另外一个有时候把很多的学习让他们能够走在老师的前面,比如我们这次国庆节的时候,就是这7天一定要把下一周,比如说按照老师要安排的计划,要讲述的一些新的知识,自己先要去学习。
比如说数学,你这个学完以后,你自己是不是能做几道练习题,这块整个自主学习推动这方面,我们从家庭作业上这块,一二年级是不布置家庭作业的,但三至六年级这一块,现在我们总共作业就占40%,还有60%的是让孩子超前去学习。
这几年就是我感觉到效果还是很好的,我那个学校孩子们学习这块在当地县也是很好的。
周轶君:最后成绩是好的。
王世民:成绩是非常好的。
梁文道:我想问一下你当初是什么时候开始这种自主学习在你们学校的实践?
王世民:我这块就从2008年就开始。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就是乡村家长这块,因为还有家庭条件限制,他也不可能让孩子去上一些好的班。
周轶君:补习班什么的,他是没有条件上。
王世民:没有条件去上好的补习班,一个是经济,另外一个方面他也没有时间,所以我这几年我是从2008年到现在我一直在做的,就是想看到更好的效果,我就是从自主学习这块突破,就是前置性学习。
周轶君:是不是大家经常会有这么一个问题,是不是反而因为在乡村,没有城市里面,比如说像补课这样的条件,或者是大家对分数的这种看重等等,反而你们会有了一些尝试一些新方法的空间。
王世民:对。比如说六年级孩子这一块,稍微好的孩子,他现在这个学期没有结束的时候,他把下个学期的那些课本都借了,他们自己利用礼拜天自己去看,然后自己去思考。我想这个就是跟苏卡塔教授这个墙上的洞。
梁文道:有类似的地方。
王世民:对,孩子自己会学的。
梁文道:我觉得这有个有趣的东西,就是今天我们国家很流行一种对于教育的假设,就是说你要不就学校要很好,学校要有很多资源,要有很多的老师,然后这个孩子学习就会好。
如果说要强调这个学生们在放学之后,或者离开学校之后,仍然要很好的有一个学习的话,那就要靠家长了,那家长要想办法搞到很多资源。那有钱的家长,就比如说送孩子出去什么游学,然后找补习上这班上那班的。
总而言之就有点像轶君刚才提到了,把孩子们时间都填满,那这个填满是首要任务,那至于谁来负责把它填满了,要不就学校要不就家长。那么我们通常都不太觉得孩子自己能够找到一些什么东西,就我们对教育的想法,尤其对乡村教育过去几年中国的农村教育,很强调加大资源,这当然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那个加大资源背后的假设,却是我们只要把更多的东西丢到学校,或者丢到家长那,让他们拿去填满学生,那这个教育就搞定了,但是看来你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您当初是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路子呢?
王世民:乡村这块,现在很多家长其实从2005年开始就是打工经济已经开始了,那好多家长特别是在小学,加上爸爸妈妈一年可能就见一次就是春节,好多特别那边是内地,他们都在沿海就是发达的地方进城去务工。
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寄宿制,为什么当时要做这个寄宿制?因为我到那个学校去以后,就是一百来个孩子在一个村,那早上有个孩子来这吃饭,他都是家长给一块钱,在路边买个小食品,拿着就到学校来了。晚上比如说有一点点学习任务,爷爷奶奶本身好多就没有文化,就上上一代人,他可能就没有文化,他也不会去辅导,所以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很多的留守儿童是一个不好的名词儿,不好听,因为四个字里面。
梁文道:有很多不同的含义进去。
王世民:它的含义就是代表人落后,不努力不奋进。
周轶君:确实有很多悲剧的发生,对。
王世民:当时去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到这个学校这样子不改变的话,我再待一年的话、待五年的话,我就觉得也没有什么意义吧,所以我就想那个时候家长缺位了,那咱就把家长他爸爸妈妈的责任,学校就把这个担过来。
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就2005年,我那个时候可能是年轻,比较胆大一点,当时就是想方设法,我们当地在关中地区,公办的那个时候,当时我们就是第一个寄宿制的学校。
周轶君:好像您跟我说到过,您会在每天早晨在校门口等学生是吗?
王世民:这一点可能在我们那个县我也是第一个吧,就是每天早晨我会是第一个到校门口去迎接师生。其实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小细节,但是我们那个乡村的学校,就是两千二百多个孩子,现在也是比较多的。
很多包括我们西安市我们一些同行的校长,包括一些上面领导来,说这个学校认识个农村学校这个孩子,就是感觉跟城镇的孩子差距不大,他们也阳光也很有礼貌很自信,这个一个是把尊重能落落到实处。另外一个,比如说对一个不喜欢说话的孩子,你老跟他讲“见了客人要问好”,一年以后他还是这样。
但是当老师五次你主动去问他的时候,第六次的时候,他可能就有意地想跟你对话。
梁文道:所以这种尊重等于是要变成细节的行为表达出来,所以这里面还牵涉一个事情,就是平常谈教育谈社会谈“赋能”,就你要把能力交予这些孩子,要发展他们的能力,因为你讲尊重其实也是一种赋能,你要让他觉得自己有自信心,他像个平常的,他跟任何别的小孩是没有分别的。
平常我们今天讲农村学校、乡村学校,很多时候大家都有一些既定的印象,就像刚才王校长您说到留守儿童一样,就是一堆既定印象,那么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怎么样把他们本来该有的能力发掘出来交还给他们,包括你刚才说的一个有自信心,一个自我学习的能力,所以这里面全都是连在一起的,是你当初就已经想好就是很系统的要往这条路走?
王世民:刚才说学习是自我自主学习。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自我管理的能力,现在我们2200个孩子上午吃饭。
梁文道:这其实是个大事。
王世民:午餐这块其实我们同行也很奇怪,我们领导也很奇怪,说你们2000多孩子吃饭,小学生小孩子吃饭也没有人去管,我说我们不用去管,我有几十个“校长助理”,到12点的时候,那么校长助理就是每个月都有轮换,他们去安排这个秩序。
梁文道:校长助理室特别请的还是什么?
王世民:就是孩子们。
梁文道:就是孩子。
王世民:我好多的行为管理让他们去做。
梁文道:他们是校长助理。
王世民:班级评价,比如优胜班级的评价让他们去做。
梁文道:然后他吃饭怎么样?那些孩子当您的助理。
王世民:这块在餐厅里边,这个校长助理比如安排这班,你在这个位置,你这个按顺序不能加塞,不能说话等等等等的这一块,所以他们管的我觉得有时候比我还管得好。
周轶君:我曾经有一次在一个学校里面,我去看他们吃午饭是要老师拿了一个大喇叭在喊,某某某组不许说话了,某某某这个我就看那个场景我觉得。
梁文道:太累了。
周轶君:太累了吃个饭,那么在印度我也参观有一个学校的时候,那个校长他让我自己挑两个小女孩,说让她们带我去参观的,有两个小女孩。
王世民:我看到那个画面。
周轶君:对,他说学校是学生的学校,真的是,所以你也是这样做。
王世民:对。
周轶君:这个跟您在美国的经验有关系吗?
王世民:2017年马云基金会组织我们首届获奖的校长去美国游学,所以在去美国之前我会想到很多的问题。我想在很多方面这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想法,其实我看完以后,我就觉得其实中美两国教育是有差异,但是我们也有我们这块的很多的好的一些做法,他们也有他们好的做法。
周轶君:您是在哪里?当时在美国哪里?
王世民:当时在纽约,在华盛顿,教育上这块,我们主要是在北卡罗来纳。
周轶君:您就专门去了一个乡村的学校当校长?
王世民:就是北卡罗来纳州下面有个巴林小学(音),在那里待了三天当影子校长。
梁文道:什么意思叫影子校长?
王世民:影子校长,就是管理者的身份,我是校长的身份,我就跟他们作息时间是一样的,开始一天的工作,比如说去教室查课,比如说组织他们下午放学呀,午餐呀,还有一些工作的安排。
周轶君:那为什么叫影子?是因为其实您不是真正取代那个校长,是这个意思吗?
王世民:是。
周轶君:就是副驾驶员的意思。
王世民:其实我在美国待的几天我就有几个细节,我现在我记忆非常深刻。一个是我去他们学校以后课间,我就发现他们那个图书室都在一楼,都是开放的,孩子们随时可以进去。
更有趣的事情是,孩子们读书是各种姿势,前提是他们那个图书室里有很多就是有摇篮,孩子们躺在摇篮上读书,躺在圆的沙发上,最自然最舒服的姿态去去读书,这件事情对我们学校现在有很多启发。
现在我们学校书也是放在他们能很容易拿到的,也给他们做了很多卡通的座椅,可以躺着的座椅,结果证明了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样书他们随时可以拿到,那个环境他们舒服很喜欢,所以就不用说要好好读书。另外一个美国孩子从小的规则制度的观念这是非常强的。
梁文道:怎么说?
王世民:他学校副校长的女儿就在那个学校上学。那个孩子也特别喜欢中国,还一直闹着要说把家里的房子农场给卖了,要到中国青海去,在网上看到的图那么美雪山喜欢那个地方,听说中国一些校长要到他们学校去,她就非常高兴。
我就觉得这个小孩很可爱,想和她拍个照,那个小孩用英文告诉我就说,说对不起老师,我们老师在那边我们要吃饭了,吃完饭跟老师说一声,过来再给你拍照,可以不可以?她是7岁,她很有规则意识。
周轶君:一方面很自由,读书什么姿势都可以,一方面它规律感又很强。
梁文道:很自律,你觉得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周轶君:这个怎么来的,我在想一个事情,我走了那么多地方以后,我慢慢的发现所谓我们说好的教育都是在两极之间掌握一个平衡,尤其规则度这些其实是跟自由是联系在一起的,你首先要给他自由你相信他,规则怎么来让他自己制定。
我其实后来在中国拍摄的时候就经历过一个事情,是他们有一个那个夏令营的活动,他们的营规是怎么制定,就让孩子自己制定,我们在一起讨论我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这很简单,每个孩子都会讲,那么在这个之上我们来制定规则的时候,孩子就愿意去遵守,因为这个规则不是由上至下强逼给你的,是我们大家都认同的。
所以我不知道您说美国那个学校它这个规则,是不是他们有某种参与来制定或者怎么样,但我自己后来慢慢发现,我跟孩子的实践当中就发现你相信他,给他一定自由,在制定规则的时候让他参与,他会自己告诉你要干嘛干嘛,他自己也能做到。
包括您刚才说的使用互联网,其实在印度看到的也是就是自由和规则也是同时的,一个是孩子自己可以玩,但你看它有规则,就是你们一定要几个人在一起,你那个屏幕足够大,要所有人看到你在干什么。
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们觉得说老师他也是在乡村非常偏远的地方,他的老师都不是什么博士,但是他觉得最关键的是老师要能问题,他们有一套方法教给老师怎么来问“大问题”,他所谓的大问题就是我不能马上直接就答出来的,他会在他们的那个网站上面有他说怎么制定大问题。这个问题一定是孩子要想一想,他自己去找答案,不必老师一定比这些学生要强。
到了后来我在印度访问另外一间学校的时候,他们不是有个电子公民课吗?这就更明显了,我上网的时候要了解什么样的规则,我不要相信我搜索到的第一个答案等等,它都是在一个放给你自由的同时告诉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律。
梁文道:那个角色变得老师不是一个给答案的人,是一个在协调学习过程的人,就是他们英文叫facilitator,他是在协调各种的教育的问题的发生,课堂的进行,而不是直接给学生答案。
不过你刚刚讲到规则,我想起来,印度恰恰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规则几乎你看起来好像是不存在的一样,那他们的教育里面比如说像刚才王校长说到在美国时候看到一个七岁小孩就会这么有规则意识,那印度我因为我在这期节目就没看到就是他们怎么样处理这一点。
周轶君:我觉得规则确实不是他们的强项。
梁文道:我觉得他们好像不太在乎这个事情。
周轶君:说到规则当然印度是没有什么规则的,就是很多时候那种变通,比如说我们去机场的时候行李超重,七个人肯定超重,对吧?我们每次的当中有一个人会说,我们那个收音师他会说,我一看谁谁谁的,就是机场工作人员的名字,我就知道他是不是亲莫迪总理的,过去一拍他,我也是莫迪的人,来吧,这个超重不用收费了。
居然十次有九次是管用的,所以他们这个当然很变通,但是他们有个规则就是大家规则是在相互磨合当中,你慢慢往前走,当然印度就是会由于它这种规则性其实不是特别强,它的效率也低,它整个社会效率也低,但它的另一面就是什么呢,没有一个力量是最强的,没有一个人就说了算。
他们告诉我在印度,比如说你公司生产一个产品出来,在中东有那么多国家,几十个国家,你只要制定四个市场,在印度他一个邦里面你可能就要分好几个市场,就变成了它相互的制约感其实特别强,没有一个人是最大的。
2019.10.28
手机扫码下载「看理想」App
参与并查看评论内容